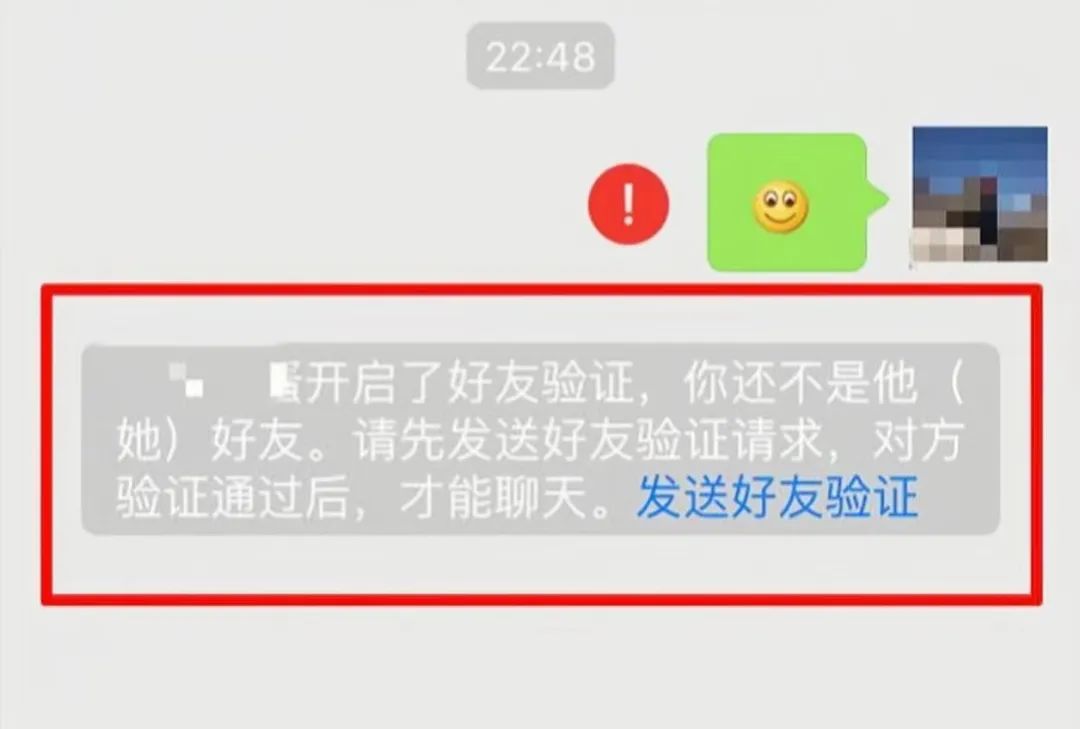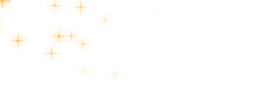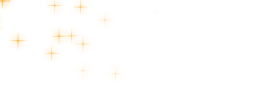“地主家的大少爷又在打老婆啦!”
双抢时节,正午时分,**辣的太阳当头照下,耀得人睁不开眼。刚从地里割禾打禾回来的人——光着油黑膀子的男人们和上衣紧贴上身的女人们汗流浃背,他们捧着饭碗,蹲在庭前小小的圆树荫下,就着不时吹来的一阵一阵闷热的风,两根筷子一声不响又无精打采的挑着自家地里长的、女儿们随便炒的几色青菜。听起来同样精疲力竭的知了,吵闹得让人类费解,不过无人在意,甚至充耳不闻。整个小村如一锅滚烫却毫无波动的死水,日复一日煮着活人,偶尔“咕嘟”冒一个泡,不知道是吞没了什么。
忽听隔田相望的坳里,传来一个女人哇啦哇啦的含浑的哭叫声,将死水一般的沉闷打破。对于女人的哭叫,这个小村的人们本是司空见惯到提不起兴致的,但今日此时,这尖锐的哭叫正好供人解乏。埋头吃饭的人们顿时来了劲头,甚至亢奋起来,像一群正在享受**的人,空气里都有了暧昧的气息。这个被大山围困的贫穷小村,家长里短互揭隐秘是众人唯一的娱乐。
“我们都累得不想动了,他还有力气打老婆。嘻嘻。”
马上有人闻言知意,脸上荡起一抹知味的笑,接口说:“到晚上,不知那猪婆还得这么哭叫几回。”
“真好味口,那样的也啃得下,哈哈……”
人们口中地主家的大少爷叫继开。现在已
是九十年代,村里早就没有了地主。四十年前,还是继开十六岁的时候,村里的最后一个地主被抓了起来,三个月后被随便处决了,那是继开的父亲。
继开恨父亲,那个既是塾师,又是地主,还兼任村中理事的骄傲的人。所谓地主家大少爷的身份,只不过在租户面前有限权力的虚假象征,父亲所给的生活的节俭,不是他们能想象的——一条二指宽的小鲫鱼,父亲独享一半,剩下的一半母亲和他们五个兄妹平分,得吃上一个星期,也从不因他是儿子而多分得一点。父亲没有给继开多少实在的享受和利益,却往他肚子里硬填了好多一无是处的废字故纸,又连累他一辈子遭逢厄运。一想到父亲,继开心中只有怒火。
“你个蠢婆娘!你怎么不去死!你个蠢婆娘!”当继开独自劳苦半日回来,看见茅草屋上没有冒烟;屋前晒谷坪的稻谷依然成推,没有摊晒开;蓬头垢面气味难闻的老婆,带着同样面貌的一儿一女有说有笑,倚门而歌。继开胸膛里的怒火瞬间**开来。他加快脚步,尽管肩上挑着满满一担谷,依然健步如少年。他不声不响地在坪里卸了担子,抽出扁担,赶到他老婆桂香后面,横背就给桂香一扁担。桂香吓得“哇”地一声跳了起来。八岁的女儿淑琼早看见父亲了,赶紧说“姆妈,快,快,快去煮,煮饭!”
听到女儿结巴,继开火气更旺了,瞟一眼门口浸泡了一上午、一滩滩洗衣粉残渍都未消融的、被太阳发酵得腥臭的脏衣服,一脚踹开桂香,冲进屋里,拔下插在土坯墙裂缝里的竹条,一把揪过女儿,一顿狠抽。
“让你结巴!你个蠢婆!**是蠢婆,你也是吗?”
“我,我,我不结,结巴了!我不是,是,是蠢……”淑琼尖叫着哭。
“**不会煮饭,我没教你煮吗?衣也不洗!谷也不晒!我让你懒啊!你懒啊!”继开忽然满腔悲愤,恨不得都化成力气发泄出来,又狠不下心。淑琼没有眼泪的干嚎,让他更加心烦。
“几件衣服,放了半袋洗衣粉,你以为赚钱容易!”继开下死劲抽了几条子,已见斑白的两鬓淌着亮晶晶的汗水。淑琼的眼泪终于下来了。
“我不放了!我不放了!”淑琼在继开手下扭动着,哭叫着。
“快去淘米煮饭!”看见女儿的眼泪,继开似乎泄了气。抬头却碰上七岁儿子三明呆滞的白眼。继开整个打人的过程,儿子都在冷眼旁观,一动不曾动,像在入迷观摩一个疯子。继开蓦然心惊。双手仿佛不受控制,竹条辟头就向儿子抽去。
三明大惊,也不会闪避,只闭上眼睛,缩起脖子,就像可以把头缩进胸腔里去一样。竹条抽在头上,三明只哭了半声,却还是杵着不动。
“还不去写字!”继开终于找回了语言,气急败坏地冲三明吼道。说到写字,继开又觉无力,连话都无力再说,胸口生疼。他也知道,儿子哪里会写字?
继开自觉儿女头脑不笨——尽管女儿有点结巴,儿子经常发呆。他始终不明白学校的老师为什么不肯收他的儿女。去年,他费尽唇舌,终于让老师收下了淑琼和三明,校长也在他的一再坚持下,收下了学费。一个星期后,老师还是劝退了他们,校长全额退了学费。理由是三明不会上厕所,一坐下就不再动,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。而淑琼从不听课,上课时总是悄悄用指甲掐同桌的手臂和腿。
继开好不容易教会了淑琼写1、2、3、7,让淑琼带弟弟一起写,他没有更多的时间,一家四口全仰赖他存活,他已年近花甲,还能照顾他们多久?
看着儿子动了起来,终于像个活物了,继开的心好受了些,他放下竹条,进屋倒一碗水,冲入一勺白糖,搅着喝下。既然还没饭吃,就先把屋前的谷子摊晒一下,再来做菜吧。
继开拿了耙子出来。桂香正歪着头站在晒谷坪前的大日头底下,脏污的脸上挂着湿痕,分不清是泪是汗,正掰着左臂撕上面的旧痂。
继开怎么也没法将眼前这个脏得像一头猪的女人,跟十年前初娶回家的那个明丽少女联系起来。当年还在做女儿的桂香虽然就是偏头,却整洁白净,高高的鼻子,深邃的大眼睛,娟秀的黛眉,鹅蛋脸上一笑漾出酒窝来。岳母操着难懂的外地方言,解释说女儿是小时候烧坏了脑子,不是遗传。
刚结婚那一年,继开怜桂香年轻,像待女儿一般爱惜着这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女子。他什么都不要她做,每天帮她梳洗打扮,甚至桂香来例假时,都是他帮她料理。后来桂香帮他传了宗接了代,他对她更是爱惜,却已力不从心,再也照顾不过来。最终,穷困与劳累消损殆尽了柔软,让他又恢复了年轻时的火爆脾气。
继开咬起下唇,一耙打下去,桂香一阵发懵,第二耙又打在了身上。
“你个蠢婆娘,老子今日就打死你!”继开动了真怒,桂香用手护着头,耙打到手背上时马上缩手,她不敢反抗,只能哇哇哭叫。
继开打累了,怒气却未平,快步进屋拿来捆禾的长麻绳。
“我勒死你个蠢婆娘!”继开声调酸涩,隐有泪意,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。
桂香怕死,开始挣扎反抗,继开勒不到她脖子,便勒住她的腰往前拖,“老子拖你到塘里浸死算了!”
桂香一**坐到地上,一边想要挣脱绳子。继开收紧绳子,桂香见挣不脱,只得双手死命按在地上,哭叫声转而凄厉,喊起了娘。
继开费了好大的劲,把桂香拖到了晒谷坪边,再沿着石砌拖下去,把桂香摔在水淹着的第二级石砌上,怒气终于被累消磨了,他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暴戾的疯子。
继开抽了麻绳返回屋里,开始做菜。桂香坐在水里哭了一会儿,自己爬起来,走到坳外的马路上,在最后能看见自己家茅草屋顶的地方停下,望向远方,一边哭,一边喊“娘啊”——除了这两个字,没人能听懂桂香哭诉里的其它。桂香的娘在桂香生淑琼的时候来过一回,抹着泪走后,再也没来看桂香。太远太远了,要坐好多车,桂香不知道娘家的地址,也认不得回娘家的路,也没有钱坐车。
路牙下住着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妇,儿女都出去大城市定居了。夫妇正在吃饭,女主人听不下去桂香凄恻的哭声,丢了碗出来劝桂香,声音酸酸的:“妹子,别哭了……”她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劝,桂香确实太不像样了。“你也勤快一点啊,你男人就不会打你了。你看你……”女人一边说着,一边撩开桂香面上湿答答粘腻腻的头发,“明天我给你剪头发啊。你要洗澡啊,衣服,洗干净啊……”
桂香嫌女人啰嗦,要是她会说这里的语言,她可能会这么说出来了。桂香知道这个女人,这个女人有什么资格说她?这个女人是个臭疯子,发作起来的时候,舞刀弄棍,喊打喊杀,见人就骂,谁都要打,被她老公绑起来关在家里,她会打破自家门窗逃出来。这个又疯又蠢的老女人,桂香不要听她的。
坳下面一个媳妇顶着破了边的草帽、挎着一篮子新摘的辣椒路过,上前劝桂香。“已别哭了,踏太阳底头,回家去吧。已看已,穿过棉鞋作什么!”
这个媳妇桂香也知道,她也有一女一儿,跟自己家的孩子差不多大,都在上学。她每年闹一次上吊,说自己男人另外有女人。他男人就说她疯了,把她绑起来关家里,一直到她不发疯了。去年她跟她婆婆吵架,喝了一瓶农药,从医院回来后,话就说不清楚了,有人说她脑子被药坏了。一个被药坏了脑子的傻婆娘,有什么资格说别人?
坳对面的那个女人也来劝桂香。这个女人跟桂香同龄,还是同乡,和桂香一前一后嫁进这个村。她也生了一女一儿,都在上学。这个女人的男人常出外打工,女人常在有月亮的晚上一边绾柴,一边哭泣,一边唱花鼓戏,唱几句哭一回。这个女人也是个疯子,发起疯来经常赤身露体往外跑,不怕臊,不要脸,还总跑到桂香家门口的水塘里来,不知道要干嘛,桂香就拿根长竹竿打她,不准这么不要脸的女人来自己家门口。
接着又路过一个经常跟她自己男人打架的患水肿的女人,这对夫妇每次打架,都要从家里一路打到大路上,嚷着要去找村支书评理。女人和男人身上的衣服都被撕扯成一条一条的布,跟赤身也没什么区别,一路打去,跟肉体展览一样,羞耻与尊严全都不顾,桂香都替她害臊。
桂香谁的话也不要听,加上她哭够了,不再哭了,也就没人来劝了,大家吃完饭抓紧休息片刻,又要开工了。
等继开吃完饭下地去,淑琼会来拉桂香回家的。
生活就是这样继续着,这个小村里的人们就是这么继续活着,谁看谁不正常?谁看谁是正常?没有人深思。
想得太多,都会疯的。

著作权归作者所有,转载或内容合作请联系作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