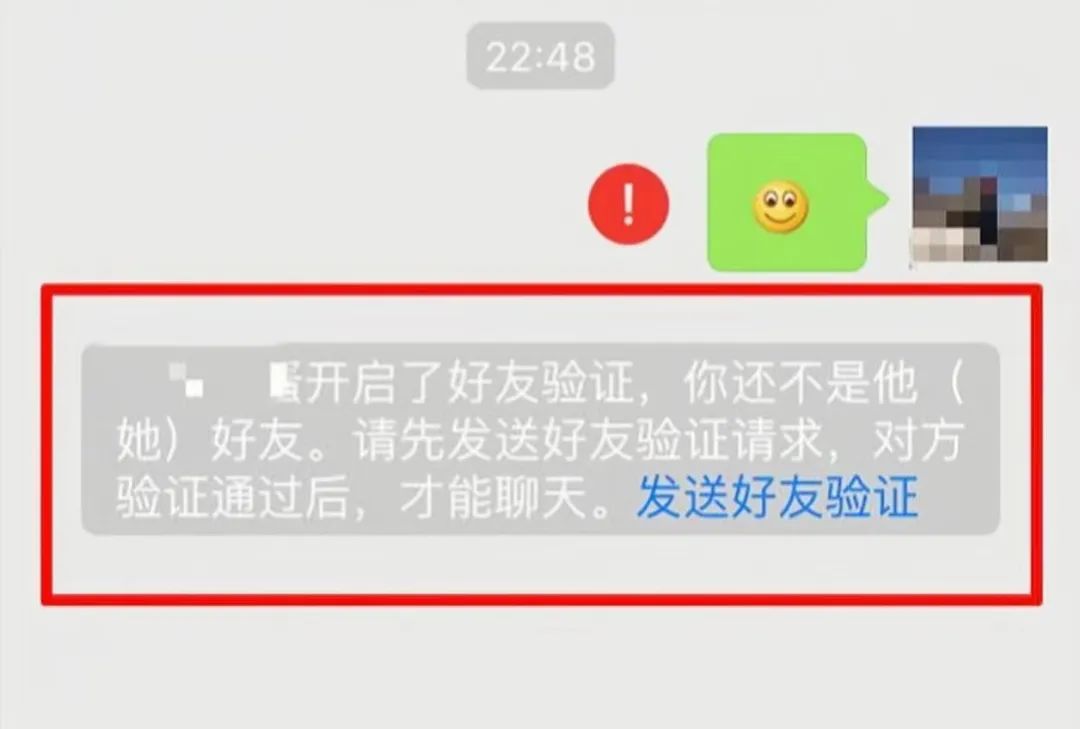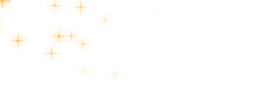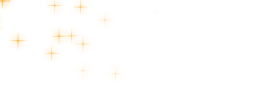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,冷漠的手术灯四面困住我的头部,就像困住一颗内蕴珍宝的石头。惨白而强烈的灯光如无数牛毛细针,刺眼生疼。我大睁着双眼,就像眼睛不是我的。我确实也无力控制,也不能凭借我的双眼看见什么。我听见“嚯嚯”的磨刀声,间着一个人“吃吃”的低笑。
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附在我耳边,幽得人毛发直竖,“我是真的爱你,你是知道的啊!”一声轻浮缥缈的叹息,令人心碎。”她们爱的是你的金钱和皮囊,只有我爱的是你。你怎么就是不肯在乎一下我呢?你难道还不相信?没关系,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嘻嘻~”
那人停止说话,眯起双眼仔细欣赏着手中锋利的、闪着银芒的东西,那是我的手术刀。我能感觉薄薄的刀刃贴上我的脸颊,轻轻在眼下部位一扎,一顿之后,又划拉着不紧不慢地往下游走,如一条冰凉的蛇翻拱着蛇蜕。有万千蠕虫沿着刀刃涌出来,密密麻麻地爬满我的脸,啮噬我的脸。
我能看见我双瞳中的恐惧,恐惧在瞳中以血丝的方式迅速生长,纠缠翻涌,双瞳不断胀大,直至占据整个眼眶。
“哈哈哈哈哈哈~~~”我听见狂笑声响起,然后是激荡无休的回声,悲凉凄厉,不似人声。一道寒光斩开我的头盖,手术刀在我的颅腔里横行——如那癫狂的笑声一般,肆意翻绞着颅内勾连牵扯的神经脉络、思想意识,也斩杀了我巨大的惊惧,让我渐趋无感,不悲不喜,无所挂碍,无有恐怖。
可是我的身体上方,分明悬浮着兀自清醒的灵魂,惊怖无力的、又麻木不仁的灵魂。它知道这只是一个梦,一年以来,它已经无数次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一个一个相似的梦境,下面那具身体有时候是操刀者,有时候是病人,从最初以尖叫唤醒身体,到现在颤栗着冷眼旁观,这个灵魂似乎已经脱离了身体,脱离了苦海。直到它看见手术刀猛然剜向交错着血丝的鼓胀的双瞳,它才不由自主地颤了一下。
身体在灵魂惨烈的麻木中平静地苏醒过来,毫不理会心有余悸,依然双目紧闭,本能地尽力克制,不发出一丁点声响。
我能听见北风呼啸着扑向紧闭的窗扉和罅隙,如锐利的箭镞,挟带破空的呜咽之声,随后“啪”的一声,沉闷的拍在窗玻璃上,窗户晃出迟钝的回响。
我能感觉风的愤怒,和奋不顾身的粉身碎骨。它一次一次地把自己拍在窗户上,伤成血肉模糊,骨血顺着玻璃蜿蜒滑下,无声的滴落尘埃。没有关系,它还是会默默捡起自己,重新拼凑,不理会支离扭曲、粗糙丑陋的伤疤,卷土重来,一次一次飞蛾扑火。一如我对冷晴的爱。
我能感觉到一丝微弱的风幽灵般扰动了一下窗帘,却无力搅动房间里毫不回应的空气。我能感觉空气自顾自地在整个房间里熙熙攘攘,窃窃私语,似笑似泣,像一个疯子。
我知道冷晴正睁着双瞳盯着我。他每次都是这样,比每天的第一缕晨光都要准时。我已经不会像一年前一样被吓到了。
一年前,我把冷晴从医院搬来我的住处,又经过那一次手术(我不想多说)。每天清晨,当我睁开惺忪的双眼,瞧见他深渊白阳似的双瞳近在咫尺,无情的紧盯着我,就像我是热源,他的双瞳是热源探测器。我在他的双瞳中瞥见无数个我。无数个我随着我受惊的情绪,在他的双瞳里沉浮冲撞,挣扎哀号。他的双瞳囚着无数个我。我不能自已的尖叫着跳起来,在冷晴的尖叫中逃出被窝……那时,我不是被噩梦惊醒,就是被冷晴的双瞳吓着。那些日子,卧室里总是回荡着我们的尖叫声。
我们不可以有四邻,我们住在高高的顶层,我们像两个幽灵生活在一层荒凉孤岛之上。
我也不再因为感觉到他的盯视而心惊了。我已经习惯了,麻木了,可以如毫不知觉一样,闭着眼睛一半清醒一半迷糊,心力交瘁的——也不能说绝望,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情绪了——只是没有希望。我枕着他冰凉的胳膊,直躺到天光亮起——就像枕在忘川的渡船上,船两旁的河水里,无数如异兽旋龟的利爪般的手臂,喑哑,密密麻麻,盲目地胡乱抓向我。冷晴是我的保护者?还是抓向我的利爪?
如今,他有多爱我啊,有多看不够我啊。他已经离不开我,不能没有我。终于。
我们的卧室大而空荡,除了一端靠墙的大床,没有任何一桌一椅、一柜一台,甚至一盏明灯都没有。湖蓝色的地板,于茫然黑暗中亭亭盛放着大朵大朵的曼殊沙华,赤如烈火。四面是冰蓝的墙,冰蓝之上浮着漫天大雪,冷静,阒寂。奇怪吗?地板是我喜欢的——或许是曾经喜欢的;墙纸是冷晴最爱的背景——或许应该说是曾经的冷晴。
什么地方突然响起“吱嘎”一声,我的眼皮不由自主地颤动,我的心颤得比眼皮更厉害。我早已麻木,可是依然准备不好面对。
房间里蓦然响起冷晴撕裂般的叫喊,凄厉而空洞,如一台突发故障的火灾报警器。回声如一群受困的兽,愤怒地在房间里冲撞撕咬。
我睁开永远慢半拍的还在迷糊的眼,同时打开天花暗槽内的冷光灯。冷晴的双瞳里顿时倒映了点点荧蓝的光,似无数磷火,煎熬着囚在他双瞳中的我。
冷晴一动不动,只是张着嘴巴,声音仿佛是从肚子里发出的,如苦夏的蝉。他是永远停留在了冬天的蝉。我一直弄不清楚他究竟还有意识残存,还是已经毫无意识。
冷晴的叫声还在持续,仿佛要将空气撕开一个巨大的黑洞,吞噬掉我们这**的生活。我拉开床侧的暗柜,手指触到一堆瓶子。都是酒瓶,都是融解了药物的酒,白酒里面是Diazepam,红酒里面是Cocaine。白酒是他的,红酒是我的。
两年前,我曾双手合十,跪在佛前,祈祷着若得冷晴,此生无憾,不悔。一年前,我亲自给他动手术的时候,不就做好了照顾他一辈子的准备了吗?或许当那辆车撞向他的时候,便是冥冥中回应我的祈祷的一股力量,这股力量为他安排好了后半生,也为我。我不能后悔。我必须将生活维持下去,因为我已经完完整整的得到了我渴望的人。
以爱之名,我不后悔。
寂静的街上隐隐传来消防车的鸣笛,冷晴突然停止了叫喊。当他被我枕着的手臂屈起来,猝然用力锁住我的脖子,越锁越紧的时候,我的心里也没有惊讶,只是突然很悲伤很悲伤,转瞬又有一丝解脱的喜悦。我努力侧过头去,看着他,我便安心,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。我想我的脸上一定有一个安静的微笑,虽然有两行清泪从我的眼角滑落,掉在冷晴冰凉的手臂上。
冷晴似有所感,锁紧的手臂停顿了一下,向我侧了侧脸,双瞳依旧一片茫然,我看见他僵硬的脸颊微微牵动了一下,纵贯眼角与嘴角的那道伤疤似一条将要苏醒的蛇。我第一次觉得他真真正正是在认真看我,虽然我知道他什么也看不见——如果一年前他能这样看我,哪怕一次——车祸的脑部手术之后,哪怕他已经没有多少自我意识了,他还是不看我——如果那时候他能这样正眼看我一次,我也不会……
冷晴似乎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,他的瞳色不断变幻,似璀璨的霓虹,我惊叹于它们竟能如此灿烂。突然,冷晴猛地抽回锁住我脖颈的手臂,抱头屈膝,身体缩成一团,发出喑哑的哀嚎。
他的意识苏醒了吗?
我的心陡然被痛苦碾压住,啃噬着,仿佛坠入了万丈深海,是身为始作俑者的自责,是再也无能为力的哀痛。心抽搐到快要停止跳动。虽然如此,长久麻木的心,第一次感觉还是真实活着。
我将冷晴环在怀里,抱住他的头,试图安慰他。
“啊~~~”冷晴终于长嚎出声,像一只溺水的鱼终于找回了呼吸。他往我怀里缩了一缩,蓦然又如触电一般,用力将我推开,一边往后躲。我像搁浅的鱼一般向他靠过去,向他伸出双手。
“啊!!!”冷晴发出惊恐而潜怒的叫喊。我并没有停,我只是想安慰他,用我希望被他安慰的方式。当我触碰到他的时候,他的头向前一扑,咬住我的手臂,狠狠地,不松口。
鲜血外涌,疼痛内噬。我的眼里瞬间充满泪水,发出一声抑制不住的**。我能感觉到冷晴上下牙床的震颤,他的牙床如咬合的机床反复咀磨我的血肉。泪眼朦胧中我看见沉凝的暗黑的血珠渗出来,上面映烁着轻浮的幽蓝的光,最后互相缠成一股蠕动的虫子,从冷晴的唇齿缝间,从我的身体里,爬出来,灼烫的,冷漠至极。
冷晴的唇如夏日的暴雨,又落在我手臂的另一处肌肤上。滚烫的,久违的唇温,令我晕眩。当冷晴的唇暴风雨般一场一场落在我的臂上,我幸福得热泪盈眶,浑身颤抖。我不知道冷晴到底咬了多少口,我看着我的手臂,它像一片刚被犁透的春日的水田,翻卷着土块和泥水。是渊黑的地狱之土,播种咒怨,生长毒蛇。
我颤抖着,高烧一般茫然无力,本能地发出不似人声的**哭叫。冷晴毫不理会,就像他失去功能的是耳朵而不是双眼。他一脸漠然无情,双曈变幻出更加莫测的色彩,荧蓝的灯光似游走在异域的闪电,在他的瞳上浮闪。他脸上的伤疤看起来是那样诡异,如一道随时会裂开的门,放出狂魔和凶兽。他血肉淋漓的嘴像一朵贪婪的泰坦魔芋之花。它的唇如毒蛇,沿着我的手臂爬行;又像农夫的铁犁,一路犁上我的脖子。
窒息与疼痛终于让我清醒,恐怖刹那占领了我的心智,迫使我发出了尖锐的叫喊——那声音,就像是冷晴的。尖叫声在房间里游荡,碰撞,回响不绝,刺激得冷晴更加疯狂,他撕咬我的咽喉,撕咬我的双唇,撕咬我的脸颊。我一边尖叫一边拼命用脚踢他,他用身体压住我。我不停用右手推他,扯他头发,没有用。
恐惧和绝望虽然不如悲哀沉重,却比悲哀锋利得多,它们不是把心填满,压实,埋葬,而是将心一把一把掏空。
我筋疲力尽,放弃挣扎,右手颤抖着软软倒下,只听一声“叮当”,如丧钟敲响。我的右手悬在暗柜中,它碰倒了柜中的酒瓶,发出一串清脆的“叮当”声。
我蓦然一惊,求生的本能让我不假思索地抓起柜中的酒瓶,向冷晴的头部砸去。我想是我力气不够,酒瓶砸在冷晴的头上,只发出“嗡”的一声响。
冷晴像一头正在进食却发现有入侵者到来的兽,从自己的食物中抬起脑袋和半个身体,翻着沾血的唇,呲着血肉淋漓的牙,从牙缝间挤出低沉的咆哮。他的瞳色剧烈变幻着,是暴怒的前兆。我的心一阵骤缩,因惊恐而起的寒冷从心中冲出,奔腾到每一根指尖。
颤栗中我慌乱地用牙齿拨开了手中酒瓶的瓶塞,向自己嘴里猛灌一口,将恐惧化作力气,,趁着冷晴尚无动作,我用尽全力吻上他的唇,趁他一惊之际将他翻到我的身下,将嘴里的酒送进他的嘴里,再将瓶子对准他的嘴巴猛灌。我听见冷晴的喉咙发出连续的吞咽声,直至他双瞳中的色彩开始变淡,我终于松了一口气,随即疲惫感袭来,随之而来的是脸上和臂上火灼一般的疼痛,浓烈的腥味让人窒息欲吐。
我们终于听见了阵阵急剧的消防警笛。我看见红黄的火舌随风狂舞着,如妖异的花在我的窗外绽放,“呼啦”有声,震荡窗扉,将破晓的天色照成血红。我还看见卧室门底的罅隙有光彩明灭不定。
汗水侵入伤口,好像血肉里有无数虫子又苏醒过来,痛苦又开始**。冷晴已然安静,他看不见,他的双瞳只能感应温度,它们又开始变幻,瑰丽奇谲,就像两朵生长的花,是那样生机勃勃,仿佛正吸取了冷晴的生命而生长。冷晴蓦然发出痛苦的哀嚎,双手抠向自己的双瞳。
我惊恐地想捉住他的手,捉不住。片刻之后,双瞳已被他生生扯出眼眶,却没有掉落,鲜血涌溢,我看见双瞳后面滴血的绞线。冷晴脸上终于有了真正鲜活的表情,却只有扭曲的痛苦。我忘记了自己的痛苦,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痛苦,哭泣着,心怀恐惧,无能为力。
我抱住冷晴,这次他没有推开我。他第一次主动回抱了我,紧紧地。他已用牙齿报复了我的手术刀,从此我们怨恨两清,我们之间终于只是最纯粹的爱情了。
我最后一次掏出胸口睡衣下的吊坠,与它对视,和解,互相释放——那是冷晴曾经的双瞳。
我的灵魂最后一次逃脱了躯体,它最后看见我手心的双瞳滚落、塌陷;看见地板上的火焰活了过来,熊熊地围绕着床上两个不停纠缠的不**形的怪物舞蹈,就像祭台下的巫舞。

著作权归作者所有,转载或内容合作请联系作者